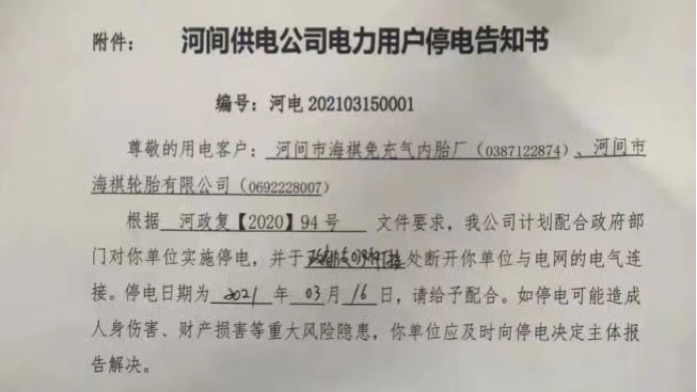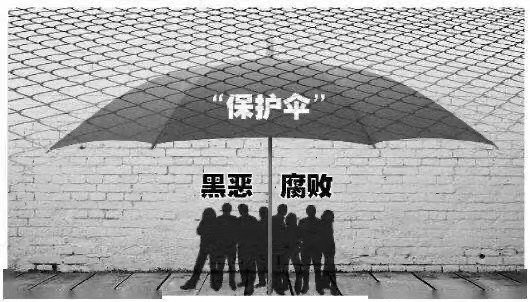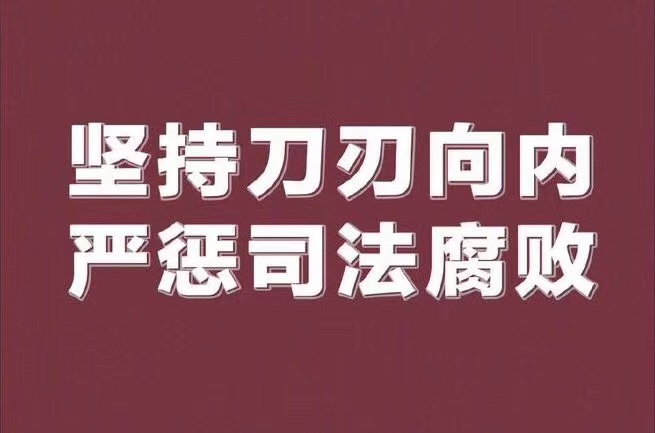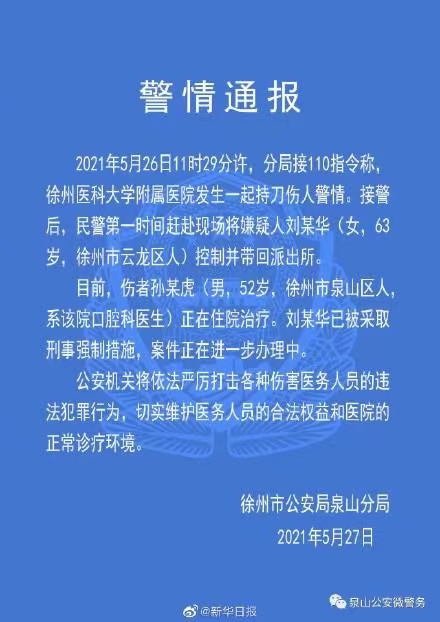司马南“炮轰”莫言,一场“文学白痴”的狂欢节

撰稿丨唐山
全文共11709字,阅读大约需要30分钟
政治是重要的,但政治不是一切,不能用政治标准套一切领域,不能因为牛顿出身富农,就说牛顿定律是封建残余,也不能因伽利略信仰宗教,就说他的发现是迷信。纳粹曾宣布,代数是犹太人的腐朽学问,几何才是希腊人的光明学问;苏联时期,李森科称遗传学说是资本主义的骗局,应予严禁,以一人之力迟滞了苏联生物学的进步。天下反智者是一家,这样的蠢事,绝不能再干了。

“碰瓷”完柳传志后,司马南(左)又开始纠缠莫言,依然采取的是无中生有、断章取义的老套路,对相关专业不需懂任何基础知识,只要冒充一下“爱国者”,就能怼天怼地怼空气。如果只需一张嘴就能把做出过实际贡献的人们按在地上摩擦,将来岂不人人空谈?
“不同意莫言所说的‘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我们这个社会总有真善美,为什么不能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那些英勇献身的英烈,歌颂祖国,歌颂母亲,歌颂爱情,歌颂美好的新生活,有何不可?司马南是坚信毛主席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思想,认为文艺就应该为人民大众服务。”
近日,“网红”司马南因在视频中两度公开“炮轰”著名作家莫言,引起“网络狂欢”,无数从没写过小说,也读不懂严肃小说的“文学白痴”们,纷纷跳出来品头论足,狂蹭流量。该事件可用三点概括:
首先,外行人说外行话,将恶意误读、逻辑陷阱、虚假命题等发挥到极致。
其次,用政治标准套文学,很多观点早被驳倒,又死灰复燃。
其三,类似的“大鸣大放”曾将我们民族拖入集体灾难中,要特别警惕它的副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文学白痴”的狂欢并非首次。2012年,莫言赢得诺贝尔文学奖,实现了几代中国作家的梦想,当时便骂声遍网,著名学者许纪霖、高尔泰、陈丹青(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者)等都发表了负面评论。只从这些评论看,他们对莫言作品理解极其肤浅,对当代世界文学发展的认识也不够深入。

著名美学家高尔泰先生曾批评莫言的创作“道义感和同情心的阙如,也就是思想性和人文精神的阙如。说了那么多农民的故事,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却不曾提到,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农民的本质身份。这不会是偶然的”。依然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理解文学。
学者如此,普通人更甚。即以贴在莫言身上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的标签为例,少有人追问:莫言的哪部作品算“魔幻现实主义”?他和阿斯图里亚斯、马尔克斯、胡安·鲁尔福、卡达莱等风格不同,是如何算成“魔幻”的呢?
事实上,在诺奖授奖词中,明确称莫言的创作是“虚幻现实主义”,被误译成“魔幻现实主义”。所以读者一提莫言,便是“想象力好”“神秘主义气息”“会讲故事”,至于缺点,用一个“脑筋急转弯”就能想到——远离现实,不为百姓鼓与呼。
2012年12月10日,莫言发表了《讲故事的人》,描述了自己的这段挨骂经历:
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地,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拨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千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
其实,人们真正接受不了的是:一个我没怎么听说过的作家,凭什么获诺奖?
于是,莫言成了最好碰的一块瓷:知名度高,人们却不了解他;他不怎么说话,甚至不太为自己辩护;作品多,容易摘出敏感句,证明他“有问题”……“聪明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我把莫言驳斥得哑口无言”“我教他怎么正确思想”等“成就”。如果“怼莫言”能提升知名度、拉流量、帮资本套现,那么,自然是人人都“怼”,越“怼”越狠。
古今多少斯文毁于此,莫言只是诸多不幸者中的一个。
▌当代文学的定义已发生剧变
确实,莫言说过:“我有一种偏见,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恶的成分。”
这给了司马南“抖机灵”的空间:文艺当然要揭露,但揭露批评应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不能为批评而批评。可莫言的观点是文学永远只能是清一色地揭露黑暗,不能有赞美。
司马南认为,他和莫言有不同的文学价值观。
这颇让人想起《好兵帅克》中,奥匈帝国的密探坐在小酒馆里怎么也不肯走,老板谨言慎行,生怕被对方抓住把柄,密探见无机可乘,便问酒馆中皇帝的画像为什么这么黑,老板说,苍蝇总在上面拉屎,给染黑了。密探立刻快活地大叫道:终于抓住把柄了——你污蔑皇帝。
事实证明,只要肯罗织,把柄总会有。
其一,文学所说的“批评”,指“指出优点或缺点”,与社会批评(专指缺点和错误进行分析并提出意见)不是一个概念。著名学者李长之写过《鲁迅批判》,曾在1966年被指为“污蔑鲁迅”,这种可悲的笑话,今天不应该再重复了。
即使莫言所说的“批评”,是指社会批评,也无可厚非。这段话出自一次演讲,莫言在前面讲作家要说真话,进而说了这番话。即使后者与前者是递进关系,也是为强调前者而“极言之”。这类修辞手法很常见,比如刘少奇同志1949年在《天津讲话》中曾说:“从发展生产力看,资本家阶级剥削是有其历史功绩的……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这段话对稳定当时天津经济产生了良好效果,也给刘少奇同志后来的人生带来极大麻烦。
事实是,具体语境中使用的语言,不能视为基本价值判断,不应上纲上线。世上最可怕的是拿两把板斧砍人者,左右逢源,唯他最公允、最全面,但这种没有操作性的“全面”,往往变成“整人”工具。
其二,这段话在学理上也没有大问题,因为“文学”的定义出现了巨大改变。今天所说的“文学”,和过去所说的“文学”,大不相同。
诚如作家李伯勇先生所说,在相当时期,“文学是社会的神经,是民族的心灵,是社会变革的前导,是教育和团结人民和消灭敌人的利器,是推进社会进步的率先选择”。可随着时代发展,这种文学已经衰落,原因是:
现代社会是高度分工的社会,文学已无法胜任传统文学的职责:只有深通政治学、行政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的作家,才可能提出相对靠谱的意见,此外还要文笔好,真要修炼到位,恐怕60岁还没毕业。回望历史,我们会发现,即使是鲁迅这样的伟大作家,他针对现实的建议也经常是粗糙的、错误的,他在“左联”时期也没能做好团结工作。在今天,“包揽一切的全才”已成传说。
文学的社会功能已弱化:在启蒙时代,文学是传播观念的主渠道,特别是小说,其独特的故事化讲述方式,大大提高了传播效率。可在今天,人类已落入“故事过剩”的环境中,电影、电视剧、广告、视频、电子游戏、新闻等都在讲故事,在传播效率方面,小说已被甩在后面——很多读者一看小说开头,就会因其虚构感,而将它扔下。
文学的领地已被分化:随着非虚构、纪实文学、新闻采访、鸡汤文、网络文学、专访、影视剧本等纷纷自立门户,今天的文学已变得相当狭窄,只剩下形式探索、文学式哲思等,即“严肃文学”,只有极少数专业人员在操练,读者阅读这种文学,不再是为了获得启蒙、建立社会意识,而是为了审美、热爱,为了看看文学的想象力还能走多远。
总之,我们今天面临的是两种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充满社会责任感的文学,卡夫卡式的、追求自我与世界本质的文学。
对于前者,司马南的“文学价值观”可能成立,对于后者,则属无理取闹。
▌文学已成角落中说风凉话的那个家伙
遗憾的是,对于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包括一些学者,没意识到这两种文学的巨大不同,他们依然带着旧文学观来看新的文学。
比如著名美学家高尔泰先生曾经分析过莫言的高处与低处,并认为:“莫言的问题,主要不是在于他究竟说了什么。那个没说的东西,比他说了的重要,也比他说了的明显突出。”
许纪霖先生则写道:“作为小说家的莫言与作为知识分子的莫言,让人感觉彷彿今年(2012年)诞生了两个人格迥异的诺奖得主。”“莫言式的生存智慧,不幸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

许纪霖先生对莫言的批评中,包含了对自己、对当代知识阶层的批评,自有其价值,但所谓“一个文学家不仅以作品说话,而且也以自己的人格见世。文学家可以超越政治,但不可以超越道德”,仍是把文学当成工具,沉迷于文学的“服务论”,则《安娜·卡列宁娜》《卡拉马卓夫兄弟》《红楼梦》等曾被认为是“不道德”的 小说,难道当初就应禁绝?
陈丹青则说:“我没看过他的作品,但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与作品无关。”
这些言论,都指向了一个可怕的事实:许多反抗者的精神深处也是高度贫瘠的、非黑即白的,缺乏足够宽容度。他们并不真的知道什么是“好”,只是坚信,否认了“不好”就会实现“好”。所以,他们无法摆脱“文以载道”式的腐朽。
身处网络时代,人人都已“24X7”地暴露在消费主义的侵袭中,文学还能载道吗?文学载上任何道,都会被其他传播工具“截胡”,转化成“抖音以载道”“小红书以载道”“公号以载道”“Vlog以载道”“图像以载道”“虚拟空间以载道”……
是的,只有不写小说,且读小说水平远没入门的司马南,才会说出“揭露批评应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不能为批评而批评”之类,绝对正确又绝对没用的废话——如果你已是全班成绩最差、老师最不关注的那个学生,班级建设会想到你吗?而长期被排斥在边缘,以你的信息量和认识水平,你提供的“建设服务”往往是添乱。
所以,米兰·昆德拉会在《小说的艺术》中,提出“小说的智慧”。

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的智慧是一种非独断的智慧,它是人类最重要的思想遗产,可以帮助我们超越现代性造成的种种偏执。
米兰·昆德拉的意思是,近500年人类进步源于“科学的智慧”,也许未来它仍将是主流,但再好的思想也不能独大,必须要有可抗衡的力量,则“小说的智慧”几乎是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了——小说的核心就是嘲讽的、批评的、揭露的、反思的,当“科学的智慧”告诉我们应该这样做,并拿出必然性证明时,“小说的智慧”至少还能在角落中说两句风凉话。
这些“风凉话”是否就是负能量呢?
首先,能量不是矢量,世界并无正能量和负能量,能量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正能量多,换个方向,就是负能量多。当时代变化时,坚守传统就意味着保守,成了反动的力量。
其次,有这样一个心理学实验(为便于叙述,以下是大概描述,对数据进行了简化处理):
几名装扮成学者的实验员,用异常肯定的语气告诉受试者,1+1=3,则75%的受试者表示同意。
如现场安排一名实验员,假扮成疯疯癫癫的答题者,他说:“1+1=4才对。”结果,80%的受试者表示不同意“1+1=3”。
即使是错误意见,即使从疯子口中说出,依然有助于人类独立思考,减少共同犯错的机会。所以,反对意见永远都需要,即使是不靠谱的反对意见。在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就是这个“疯子”,它让这个“科学的智慧”垄断的世界不至于崩溃。
了解了这些,重温莫言所说的:“我有一种偏见,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恶的成分。”就能明白,这是基于当下对“文学”的重新定义而形成的思考,绝不是外行拍拍脑袋就能听懂的。
▌我们心中的恶俗,是如何被培育起来的
为什么在中国,专业学者也会忽略两种“文学”的巨大不同呢?
首先,我们错过了“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卡夫卡”的论战。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现代派”在中国大陆崛起,一度引起文艺理论界狂欢,学者们开始关注从“写什么”到“怎么写”之变。
严格来说,“怎么写”才是文学,李白的所有题材,别人都写过,“写什么”并没让李白独特,真正让李白成为唐诗冠冕的,是他的“怎么写”。毕竟,李白创造出鲜明且极具个性化的风格。
中国现代小说虽有桐城、北京八旗小说两脉,但整体上移植自西方,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经典,但真能读其文笔的人寥寥无几,中国读者喜爱的是他的“内容”,而“内容”往往是阐释的产物,阐释会不断创造出新的深度。所以,作为模仿者,很难通过否定,更进一步。
中国文学圈没注意到西方文论史上“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卡夫卡”的大讨论,这次讨论重塑了什么是文学真实、什么是经典、文学向何处去等的标准,从而用现代主义颠覆了传统写实主义。而我们仍坚守着旧标准,以为西方文学正走向颓废、没落……

卡夫卡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这被概括为:“巴尔扎克手杖上刻着:我能打败一切;卡夫卡手杖上刻着:一切能打败我。”卡夫卡呈现出文学对现实世界的无力,而人在受造中,丧失了自我,成为自己所创造出来的种种约定的奴隶。
其次,社会发展滞后,几代中国读者无法理解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崛起于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战争让欧美读者对启蒙主义所坚守的理性、人文主义的信心开始动摇——新世界并没到来,反而是人类差点集体灭亡。我们能否靠理性组织起来,能否形成集体理性?已成无解之谜。
现代主义直面人的异化,当我们越来越像社会的、机器的、环境的、经济的附属品,且无法按下逆转键时,明天会是什么?谁在操纵谁?自我真的存在吗?我为什么活着……种种追问,将我们逼入角落中。
然而,对于当时正从前现代社会向近代转型的中国人来说,这些议题过于玄幻。我们在呼唤理性,西方人在质疑理性;我们在改造社会,西方人在挣脱社会;我们在拥抱消费主义,西方人在排斥消费主义……这造成了我们对现代文学的不耐受。从一开始,我们就把卡夫卡的创作当成哲学小说,只与深奥有关,与真实感受无关。
当欧洲小说排斥线性叙事,反对过度清晰,排除小说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时,这些恰恰是我们追求的。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名,最极端时,我们的创作甚至连“好与坏”的矛盾都取消了,因为社会主义没有坏的,只有“好与更好”的冲突。于是,没有讽刺,没有社会问题,没有缺陷,没有人性的幽暗……文学成了廉价的安慰剂。
其三,教育固化了传统文学观,以为它是唯一真理。
当代语文教育以死记硬背和不断考试为基础,为了便于考试,发明出“段落大意”“中心思想”“语法”等,可谁读小说会分“段落大意”“中心思想”?谁写小说会严守“语法”?语文教学不过是分配资源的工具,与实际应用脱离。
更可怕的是,当代语文教学刻意比附科学,创造了大量似是而非的观念。
比如,文学应呈现人类精神中光明的一面,可《安娜·卡列宁娜》写的是出轨,《红与黑》写的是不择手段往上爬,《简·爱》写的是霸总,《娜娜》写的是高级妓女,《水浒传》是诲盗,《红楼梦》是诲淫……难道要将这些名著一禁了之?
文学正确与政治正确、道德正确不是一件事,彼此标准完全不同。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经过一夜苦思,终于发现真理——作为革命者,保加利亚同志讲黄色笑话是不对的。如果每本小说都如此,人类还有必要看小说吗?

莫言曾回忆自己当兵时的“文学梦”的破碎,他写道:写了一个话剧《离婚》,写与“四人帮”斗争的事。寄给《解放军文艺》。当我盼望着稿费来了买块手表时,稿子又被退了回来。但这次文艺社的编辑用钢笔给我写了退稿信,那潇洒的字体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摇头摆尾。信的大意是:刊物版面有限,像这样的大型话剧,最好能寄给出版社或是剧院。信的落款处还盖上了一个鲜红的公章。我把这封信给教导员看了,他拍着我的肩膀说:“行啊,小伙子,折腾得解放军文艺社都不敢发表了!”我至今也不知道他是讽刺我还是夸奖我。
我们的文学教育没给孩子以更宽容的胸怀、更多元的思考、更丰富的心灵,反而培养出许多虚情假意的朗读家。按语文大纲要求,学生应“深情地、缓慢地”朗读各种课文,假装自己身临其境。有幸在网上听过司马南朗读《将进酒》,做作、浮夸、装腔作势到令人作呕——这不是司马南的问题,而是语文教学的问题,乃至当代许多文学的问题——将夸张、滥情、虚伪和肉麻当成有趣。
恶俗之后,众生皆不知美。所以司马南觉得碰瓷莫言,并不是有辱斯文。
▌从“种的退化”,打通东西的情感隔阂
问题的关键,在于司马南们从没读懂过莫言,虽然嘴上说莫言作品“美”,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美”。那么,该怎么欣赏莫言的创作呢?许多读者将鲁迅与莫言对立起来,站在鲁迅的角度来批评莫言,但事实上,莫言创作并没背离鲁迅之路,而是对鲁迅的发展和延伸。
鲁迅先生处在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时代,旧文明与新文明在两个方向上撕扯着他,即:“我自己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度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周作人也多次撰文提到在他身上有两个鬼——“绅士鬼”与“流氓鬼”。
鲁迅先生向往“清明秩序”,所以他喊出“救救孩子”。
莫言则不同,他意识到对“清明秩序”的追寻才是悲剧的核心,所以在《酒国》中,写的是“吃吃孩子”──烹饪课堂上的美食料理“红烧婴儿”。
总有一天会有人出来收拾你们这些吃人的野兽。女守门人的话让我的心灵感到一阵震颤,谁是吃人的野兽?难道我也是吃人野兽队伍中的一员吗?酒国市政府要员们在那道著名大菜上席时的话涌上我的心头:我们吃的不是人,我们吃的是一种经过特殊工艺制成的美食。
厨师是铁打的心肠,不允许滥用感情。我们即将宰杀、烹制的婴儿其实并不是人,它们仅仅是一些根据严格的、两相情愿的合同,为满足发展经济、繁荣酒国的特殊需要而生产出来的人形小兽。……它们不是人,它们是人形小兽。……它们在本质上与鸭嘴兽没有区别。
说莫言的创作缺乏批判性,不关注小人物的痛苦,那是没看过他的《十三不靠》《四十一炮》等,但莫言不相信理性主义是解决之道——如果理性是对的,人类怎会打两次世界大战?怎会有几乎爆发的核战争?理性既没消除人性恶,也没带来持久和平——毁灭是理性自带的BUG,它正在阉割人类。
在作品中,莫言建构出这样的史观:个性奔放、敢爱敢恨的“我爷爷”和“我奶奶”;高度理性、只会委屈自己、毫无光彩的“我爸爸”;充满迷茫的“我”。
杂种高粱好像永远都不会成熟。它永远半闭着那些灰绿色的眼睛。我站在二奶奶坟墓前,看着这些丑陋的杂种,七长八短地占据了红高粱的地盘。
通过对“种的退化”的忧虑,莫言打通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区隔,一起站到了现代主义的立场上——原来,来自中国的相关叙事如此有力,它印证了世界文学经验,并丰富了它。
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看,莫言的高度超过鲁迅,鲁迅的创作更适合东亚,莫言的创作则能感动更多人——毕竟,“种的退化”如“阿Q精神”,是全球各地都会出现的困境。

《莫言作品典藏大系:1981-2019(全26册)》
作者:莫言著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7-01

扫码下单
▌抓住这四点,才能读懂莫言
对莫言诟病最多的,莫过于他的文体,很多人认为,其中夹杂了太多脏话,而这些脏话对塑造人物形象、推进情节毫无价值。
其实,塑造典型人物、推进情节等,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套路,并非莫言的关切。莫言小说情节很简单,许多改写自传奇故事,莫言写人亦不求生动,而是追求复调感——将错觉、色彩、声音、历史、心理活动等叠加在一起,俨然是角色的一生在那一瞬间爆炸,在这种充满张力的情绪团压力下,故事呈线性发展,进入下一个情绪团。
所以,第一点,在莫言小说中,故事、人物只是路标,真正魅力在一个个情绪团的持续爆破,每个情绪团都如此完整、如此独特,赋予莫言小说独特的美感。
比如《檀香刑》中的刽子手赵甲,为了写他身上带的阴气,则是:
他的身上,散发着一股凉气,隔老远就能感觉到。刚住了半年的那间朝阳的屋子,让他冰成了一个坟墓;阴森森的,连猫都不敢进去抓耗子。俺不敢进他的房子,进去身上就起鸡皮疙瘩。……为了防止当天卖不完的肉臭了,小甲竟然把肉挂在他爹的梁头上,谁说他傻?谁说他不傻!公爹偶尔上一次街,连咬人的恶狗都缩在墙角,呜呜地怪叫。那些传说就更玄了,说俺的公爹用手摸摸街上的大杨树,大杨树一个劲地哆嗦,哆嗦得叶子哗哗哗响。
再如《丰乳肥臀》,上官鲁氏之死时,作为一生辛苦的普通人,她是这样结束的:
母亲双手扶着膝盖,端坐在小凳子上,她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一丝风儿也没有,满树的槐花突然垂直地落下来。好像那些花瓣儿原先是被电磁铁吸附在树枝上的,此刻却切断电源。纷纷扬扬,香气弥漫,晴空万里槐花雪,落在母亲的头发上、脖子上、耳轮上,还落在她的手上、肩膀上,她面前栗色的土地上……
这几乎是诗,每一句和上一句都没有必然关联,也不指向人物性格、不暗示情节发展。如此多的情绪团构成了小说,有时莫言会彼此挪用,由此带来大量“互文”现象。
莫言真正让人震撼的地方在于,写了这么多精彩的情绪团,可他依然能写出新的。莫言有一种深度的激情,使他能经得起如此消耗。这激情来自土地,来自对生命意志的体会。
从八月底开始,秋雨绵绵,高粱地里黑土成泥,被雨水沤烂了的高粱秸有一半倒在地上。脱落的高粱米粒都扎根发芽,高粱穗子上的米粒也一齐发芽,在衰朽的灰蓝色和暗红色的缝隙里,拥挤着娇嫩的新绿。高粱穗子像蓬松的狐狸尾巴一样高扬着,或是低垂着。夹杂着大量水分的浅灰色乌云从高粱地上空匆匆忙忙飘过去,使高粱地里滑动着一团团朦胧的暗影。
第二点,每个作家都能写高潮段、抒情段,而莫言可以持续写,能把情绪团摞着用。而能达到这种源源不断、持续亢奋的状态,则与莫言小说的“结构”有关,它保证了抒情的密度与持续性。
在《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中,莫言说:
结构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形式,它有时候就是内容。长篇小说的结构是长篇小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家丰沛想象力的表现。好的结构,能够凸现故事的意义,也能够改变故事的单一意义。好的结构,可以超越故事,也可以解构故事。前几年我还说过,“结构就是政治、如果要理解“结构就是政治”,请看我的《酒国》和《天堂蒜薹之歌》。我们之所以在那些长篇经典作家之后,还可以写作长篇,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在于我们还可以在长篇的结构方面展示才华。
把结构当成“政治”,是莫言创作中不易被发现的精妙处——他不是在讲故事,决定莫言小说情节变化的并非合理性,而是结构需要——这么写,更好玩一些。
西方文论界曾有较大争论,有的学者认为,莫言小说只有故事和人物,它们都很荒唐。但也有学者指出,那些荒唐其实是隐喻,体现了被扭曲后的认识。
第三点,隐喻确实是莫言小说的突出特色。
所谓隐喻,即“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不仅在语言里,也在思维和行为中。我们藉以思想和行动的日常概念系统,基本上是隐喻性质的。”比如我们说经济形势向下,隐喻着“向下”是“不好的”。我们生活中的绝大多数观念,都是通过隐喻传达的,而莫言小说的隐喻有特别的沉痛。
比如《丰乳肥臀》中:
上官金童拼命咀嚼着柳叶子和柳枝,感到这是被遗憾地遗忘了的美食。他感到它们是甜的,但后来他尝到柳叶和柳枝是苦涩的、无法下咽的,人们不吃他们是有道理的。他拼命地咀嚼着甘甜的柳枝和柳叶,眼睛里满含着泪水。
柳叶是苦涩的,可对于饥饿的孩子来说,它是甜的,因为他们没吃过真正的甜的东西,所以,苦的隐喻被改变了。
被认为是莫言写得最好的一部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中,他这样隐喻着自己。
墙角上站着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子。孩子赤着脚,光着脊梁,穿一条又肥又长的白底带绿条条的大裤头子,裤头上染着一块块的污渍,有的像青草的汁液,有的像干结的鼻血。裤头的下沿齐着膝盖。孩子的小腿上布满了闪亮的小绝点。
第四点,“狂欢式写作”,莫言会突然将议论、刺激、脏话等元素迭加起来,带有一种发泄的意味。
比如《红蝗》的这段描写,曾震惊文坛。
在奔跑过程中,我突然想起了一位头发乌黑的女戏剧家的庄严誓词:“总有一天,我要编导一部真正的戏剧,在这部戏剧里,梦幻与现实、科学与童话、上帝与魔鬼、爱情与卖淫、高贵与卑贱、美女与大便、过去与现实、金奖牌与避孕套……互相掺和、紧密团结、环环相连,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
这些粗鄙的情绪团,体现了以自我为掩体的抵抗后,挥之不去的虚无感。不否认,这种孩子气的反抗有时破坏了小说的均衡,但它也创造出陌生感——所谓美,总会以陌生感为前提。

《莫言经典收藏》-全十二册
作者:莫言 著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01-01

扫码下单
▌形式有时就是一切,形式游戏天然正确
沿着情绪团、结构、隐喻、狂欢式写作,便基本接近了莫言小说的内核,才知道它为什么能如此打动心灵,那么,莫言为什么不能好好写呢?搞这种文体游戏有什么意思?
这就像核雕。同样是雕塑,有人喜欢雕石头,有人喜欢雕木头,但总会有人看上一枚桃核,要在方寸中展现才华,只有做出成品后,我们才发现——它确实有特色,石雕、木雕难以替代。李白不是只写剑拔弩张的句子,而是剑拔弩张的句子放在李白的诗中,绝不突兀——这就是写作者的能力。
在艺术的世界中,形式就是一切,形式游戏天然正确。每个作家的最终目标,都是找到适合自己的形式——即找到自己的声音。鲁迅的声音、老舍的声音、赵树理的声音……都是不可替代的。对于作家来说,最大的痛苦是好声音都被别人占据了,找不到自己的专属。
米兰·昆德拉曾说,人多姿势少。人类太多,好姿势太少,有的姿势贯通千年,在一代代的人身上浮现,但它只在刹那间,才露一下头。
文学太多,风格太少。追求风格绝非炫技,更不是等而下之的文学。学者赵勇曾这样批评莫言:“鲁迅是不断地自我怀疑,而今天的人(指莫言、余华等)显然比鲁迅更知道体察得失,感悟进退之道。”“过分讲究结构,过分注重形式,过分在意‘怎么写’,而不是‘写什么’。而每一次‘炫技’的成功,也意味着自我保护技术的又一次完善。”
其实,这种批评依然是用文学之外的标准来评判作家,可作家真是合格的社会家吗?作家装做社会家,如果犯错了,怎么办?
在司马南的“炮轰”中,也采取了类似的伎俩。
其一,从诺奖颁奖词中找出有歧义的话。比如“一个这样的国度,那里驴子和猪的叫嚣淹没了人的声音”“他给我们展示的世界没有真相,没有常识,更没有怜悯,那里的人们都鲁莽、无助和荒谬”,暗指莫言靠揭露中国的阴暗面,讨好西方,才获诺奖。
想暴露阴暗面,根本不用诉诸虚构,直接曝光,加上大量评论,岂不“短平快”?这样的作家作品汗牛充栋,引起的反响更大,为什么诺奖不授予他们呢?这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式的深文周纳,堪称是最恶劣的文风。通过过分解读、恶猜动机、诛心之论、自造逻辑,其中每一步都毫无实据,用排他性的反问来定罪。
世上绝大多数事,“是”的反面不是“非”,而是更多元的选择。世界与人生有太多不确定,用非此即彼来挤压,必然引发暴力。
其二,找到莫言一篇散文,称“赞美日本”,进而反问:你以文学不能赞美为名,不赞美中国,可为什么赞美日本?
这种比附亦属酷吏手段,在今天,纯文学的顶峰是小说,散文、随笔很少受关注,能否算文学,不同人看法迥异。如果散文也算文学,则莫言写过许多赞美家乡的散文,岂能视而不见?单拿一篇写日本的散文说事,有挑动民族情绪之嫌。
政治是重要的,但政治不是一切,不能用政治标准套一切领域,不能因为牛顿出身富农,就说牛顿定律是封建残余,也不能因伽利略信仰宗教,就说他的发现是迷信。纳粹曾宣布,代数是犹太人的腐朽学问,几何才是希腊人的光明学问;苏联时期,李森科称遗传学说是资本主义的骗局,应予严禁,以一人之力迟滞了苏联生物学的进步。天下反智者是一家,这样的蠢事,绝不能再干了。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作品系列-(共16册)》
作者:莫言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11-01

扫码下单
▌由“炮轰莫言”想到的
老舍先生刚写出《茶馆》时,导演焦菊隐予以退稿,说只有第一幕不错,可否扩展成全剧?老舍先生回应说:行是行,可那样不就“靠”不上了吗?
自1949年归国后,深谙“宣传之道”的老舍先生写了《龙须沟》《方珍珠》等,还有大量快板书、黑板报、岔曲之类,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即快板书《陈各庄上养猪多》,他知道写东西需要“靠”,即和宣传需要结合起来。
在焦菊隐的坚持下,老舍写出代表作《茶馆》,因没“靠”上,一时无法公演,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才登上舞台,引起轰动。老舍先生晚年计划写三个大部头,可惜《正红旗下》刚开头,便投湖而去。翻开《正红旗下》,会惊叹于它的文本质量之高,如能完成,应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颗灿烂的明珠,即使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衡量,也称佳作。可惜,这已是无法挽回的遗憾了。
写出一部好作品很难,毁掉它却很容易。好社会应该鼓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把外行的影响屏蔽在外。
从司马南“炮轰”莫言的事件中,有几点让人恐惧:
首先,纯外行坦然讨论行内事,却能引起巨大反响,将吃瓜群众绑架成为“判官”。
其次,戴着有色眼镜看文本,一有不满,便夸大其词、上纲上线。
其三,政治标准衡量一切,断章取义。
其四,一番热闹过后,没产出任何真东西,也没解决任何真问题,只提升了少数人的知名度。
其五,任性解读,可两解的地方务必单一解读,有罪推断。
其六,口号判断一切,处处追问立场。
其七,扣帽子、打棍子的传统手法。
以上种种,曾给我们民族带来过深重灾难。在今天,决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一切野蛮的、无理性的、上纲上线式的批评,都是人类文明之敌,它最终目的是唤醒人类心中的“流氓鬼”,吞噬掉我们每个人。
参考文献
《吃人,恋尸,逆伦:后革命时期以降的非理性叙事》,作者:黄文钜,《中国文学研究》第39期,2015年1月,第259页—300页。
《文学和社会意识的撕裂——莫言获诺贝尔奖激发的争论》,作者:李伯勇,《新地文学》第23期,2013年3月,第117页—127页。
《作家的精神状况与知识分子的角色扮演——以莫言与韩寒为例》,作者:赵勇,《新地文学》2014年秋季号,第98页—第117页。
《莫言小说的诗性叙事与当代诗化小说》,作者:郝丽姣,《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0卷第6期,2021年12月,第86页—第93页
《莫言小说的虚幻现实主义》,作者:董国俊,兰州大学2012年比较文学与中国当代小说研究博士论文,2014年6月。
【免责声明】文章来源于「燕京书评」公号,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侵权请后台留言,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删除;我们对文中观点保持中立,仅供参考、交流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