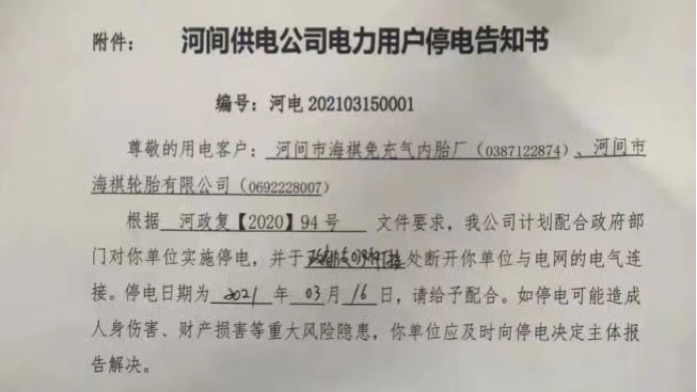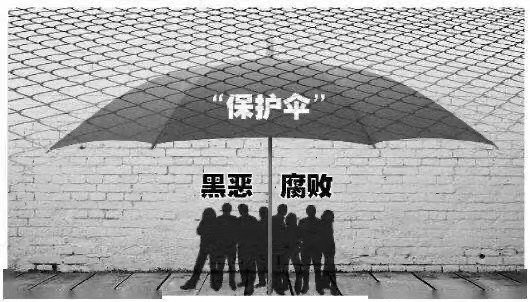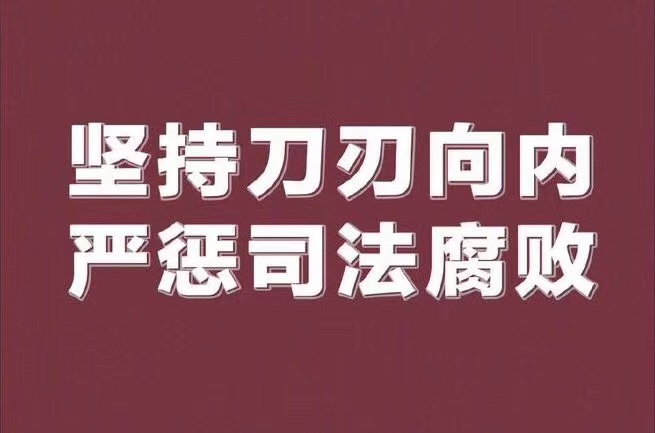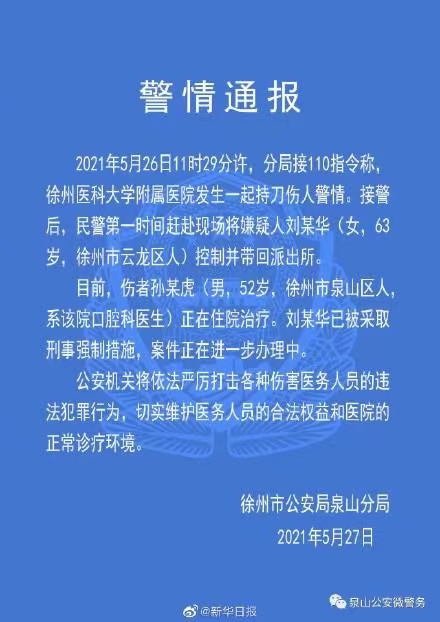他们对人性的复杂不感兴趣


弑母的吴谢宇日前二审被判死刑,因为有人问起我的看法,我在小号“维舟的方舟”发了两篇分析他心理的旧作。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悲剧,且这一悲剧在中国家庭里程度不等地普遍存在,那一家人虽是极端个案,但并非孤例。
有人读后深感共鸣,但我也注意到,另一些人对此非常不满,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心理分析倒像是在为罪犯开脱,显得他之所以犯下如此滔天罪恶,都是“情有可原”的。
不止一个人跟我强调,即便亲子关系过于密切、家庭气氛封闭压抑都是事实,“但难道这样就能杀人?”弑母的现实摆在那儿,还有什么可说的?这么一来,任何对他弑母动机的挖掘、解释,都是在有意无意中合理化他的行为,是不可容忍的。
尤为让他们气愤的是,将这一悲剧的根源归结为谢天琴的控制欲,像是在指责受害者,在往已经不会说话的受害者身上泼脏水。这特别能激起女性的同情,因为在她们眼里,谢天琴的身份不仅是个家长,更重要的,是一个身为受害者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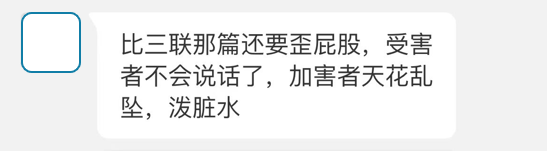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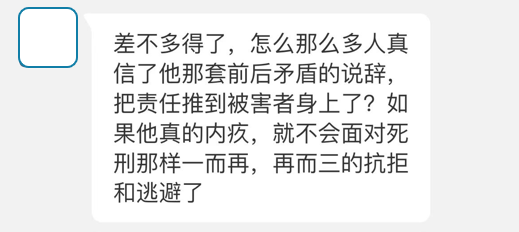
那这么说来,这事应该怎么理解?在他们看来很简单:吴谢宇就是个冷血、危险的反社会人格,不能以任何他人的行为来自我辩解,“人渣哪都有,难道都要父母负全责吗?”
在这背后,隐藏着一种绝对化的道德观:受害者应当纯洁无辜,加害者则十恶不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凶手无可逃避地承担全部罪责。对受害者的强烈同情和对加害者的道德厌恶是一体两面,并给出了一个有吸引力的简洁解释:坏人之所以做下坏事,是因为他本质上就是个坏人,只不过现在终于暴露了。
按照这种道德直觉,对坏人不需要理解,只需要你有判断力;要防范悲剧重演,也不是靠反思背后的结构性问题,而只须能迅速、准确地识别出这些人渣,离他们远一点,必要时狠狠打击他们。
这种道德义愤当然完全可以理解,但如果把挖掘杀人动机仅仅看作是在为凶手开脱,那整个犯罪心理学都可以作废了。也许违背他们直觉的是,如果真按他们的想法去做,厉行一种更严苛的道德观,不仅无法解决问题,反倒可能加剧问题。
我有一个感觉:虽然说起来都知道“人性是复杂的”,但实际上很多国人对人性的复杂不感兴趣,而本能地更喜欢道德审判。
茨威格曾有一句格言:“对我个人来说,理解别人远比审判别人更为快乐。”早年读到时也没特别的感觉,直到近些年我渐渐意识到,这其实也是一种罕见的品质,仔细看看我们周围,“审判别人比理解别人更为快乐”的人,比比皆是。
说到这里,或许会有人反唇相讥:“那你说别人更乐于审判他人,难道不也是在对这些人进行道德审判?”别误会,我的兴趣在于理解他们,不然我根本就不会注意到这个问题,进而去分析它了。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对人性的复杂面不感兴趣?很大的原因之一,当然是节省精力:想去了解他人的复杂人性,那是高投入,对陌生人的解读套用简易模板进行归类即可,或许还能更高效地避开风险,毕竟,简化才有效率。
在这种情况下,理解人性之复杂毫无必要,不仅浪费时间精力,更糟糕的是,有时还可能是陷阱:所谓“理解即原谅”,你或许会因为理解了对方的复杂处境,而错误地对他们产生了同情,这就可能动摇了自己原有的道德信条。
动摇原有道德秩序的,往往就是一些难以界定的案由,这原本可以引发我们对现有社会问题的深入反思,进而看到调适、改变的可能,然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首先引发的是一种本能的不适感,因为这意味着他们长久以来的信条和立场面临威胁,更愿意拥抱“道德确定性”,那是他们生活秩序的锚。
在这一意义上,人们之所以抵触去理解他人的人格复杂性,是因为他们其实害怕受到“污染”。这种防御性反应当然情有可原,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守护自己信念的办法,是拒绝去倾听和理解——那就像是在说“管你说什么,我认定你本质上是个坏人,你说什么我都不会信”。
本来,人无完人是个很简单的道理,但在社会现实中,一旦你的脏事引发众怒,那就一路黑到底了。像逼死前夫的翟欣欣、杀夫后冰柜藏尸的查某这类“魔女”,其实我很好奇她们为什么变成这样,想必其内心相当复杂,但我发现舆论场上就只是使劲骂,似乎任何迹象都只能表明她们在本质上早就坏透了,而最后的结论就是“避开这样的魔鬼”。
在此也能看出我们这个社会运行的逻辑:不喜欢复杂的人性并不只是个人情绪,集体行动的逻辑也是非黑即白地看待,而最终的办法就是把当事人彻底黑化,进而与之切割——他们就像社会肌体被感染的病变部位,要么被切除,要么被彻底孤立,由此确保共同体的纯洁性。

因此,在遇到这样复杂难辨的事件时,很多人的本能反应是确保自己站在“道德多数派”这一边,而非试图去探究当事人行为的根源,因为和捍卫道德信念相比,此人的个性如何无关紧要。对于日常的社会交往来说,他人的内在矛盾也无须理会,很难成为关注重心。
这样,每次出现这样的个案,对很多人来说不是一次理解那些痛苦灵魂的机会,更谈不上深入反思社会病症,倒不如是提供了一些道德教训,做好风险管理。
我听不止一个人说过,看到那些案子,就觉得现在的社会太可怕了,但之所以还在关注,就是为了让自己和家人学会辨别那些坏人,万一遇上了至少及时止损。
也就是说,如何看待所谓“人性的复杂”,实际上取决于价值取舍。投入精力去理解他者,对许多人来说是不必要的负担,甚至是有害的好奇心,可能导致自身道德立场的模糊。虽然这也有代价,无助于理解人和社会的复杂性,但对一些人来说,这点代价没什么,或许根本没意识到这是代价。
换个角度来看,深入探究“人性”的那种兴趣,恐怕本身就是现代化的结果。传统社会在意的是“德性”而非“个性”,过往的无数通俗文艺之所以总是劝善惩恶,就是因为它还扮演着一种社会功用。
这不独中国如此。张秋子《堂吉诃德的眼镜》一书认为,西方古典时代的文学着重刻画的是“行动”,而不是主角本人,其性格如何也不是重点描述的对象,直到18世纪的启蒙时代,终于诞生了以“个性”为中心的“自我”。在那之后,现代社会才出现了我们熟知的现象:在描述一些罪犯生平时,“总喜欢挖掘原生家庭、情感偏好、成长经历等,似乎这些促成个性的元素是导致犯罪悲剧的原因”。
也就是说,只有当人的主体性得到确立,他的个性才取代外部因素成为其行为的根源。当然反过来说,既然这是历史地形成的,那么,“对人性复杂的兴趣”本身也是可以被解构的,毕竟它也只是一种相对晚近才形成的视角,为什么非得要这么看待?
我想这是因为,不管我们是否喜欢,现代社会已经越来越复杂,生活在其中的个体自然也协同进化,此时,仍然试图用以往那种熟人社会的道德观来把握现实,可能本身就是不现实的——它虽然能让我们迅速做出直觉反应,但未必是理解问题的最好方式,有时甚至是误导人的。
回到吴谢宇弑母案来说,这人本身就是一个内心欲望冲突剧烈的矛盾综合体,按我一位朋友的洞察,其真实的内心可能比他在法庭上的自供更为复杂幽暗:
我觉得他说的是真心话,但是人的真心完全不必自洽,他想摆脱母亲也是真心,他赌徒式的自利也是真心。他的行为不是能够用理性逻辑完全自洽地解释的,而是多重不同情感不同估算联合作用下出现的一种(并非必然的)行为。他内心那种巨大的羞耻感和不自信让他很难真正理性地利益最大化地为自己做选择。
他弑母并不是真的出于恨,而是一种爱恨交织他自己又无法面对又不知道怎么摆脱的极其复杂的情感。其结果,一个二十多年把自己规训得那么好的能够高度理性行事的人,竟然选择了最不理性的方法。
因此,在她看来,不能想为他找到一个逻辑完美自洽的心理—行为因果链,“吴谢宇可以被理解成一个亲自下手杀人的伊万(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知识分子老二)和他大哥的合体,或许再加上那个确实杀了人然后上吊自杀的私生子。吴谢宇是个很好的小说素材,值得再来个老陀写一写。”
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初写《卡拉马佐夫兄弟》,确实也是受当时一起大学生杀人事件的触动;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的起因,同样是因在报上读到一起少妇自杀事件。现在想来,之所以那个年代的作家能创作出这样的作品,也是因为社会现实激发出了他们对人物复杂内心的深入探究。
对我来说,像这样的极端个案并不只提供道德教训,它还让我们看到: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悲剧。在这一意义上,理解那种人性的复杂,也就理解了社会的复杂,而看清了社会的复杂之后,我们才能理解自己所身处其中的现实。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并不只是“兴趣”,其实还有勇气。借用康德的话说,我们要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性。
作者|维舟
来源|公号@维舟的方舟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好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致信jinrizhiyi@gmail.com,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