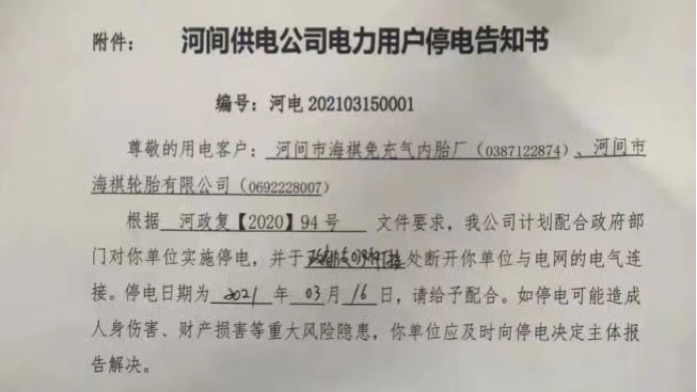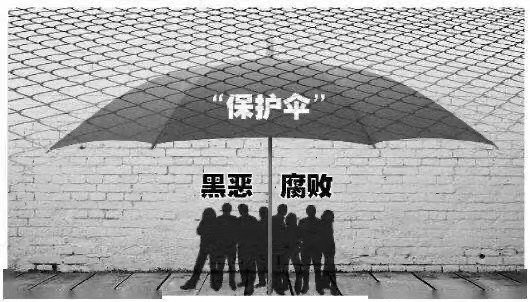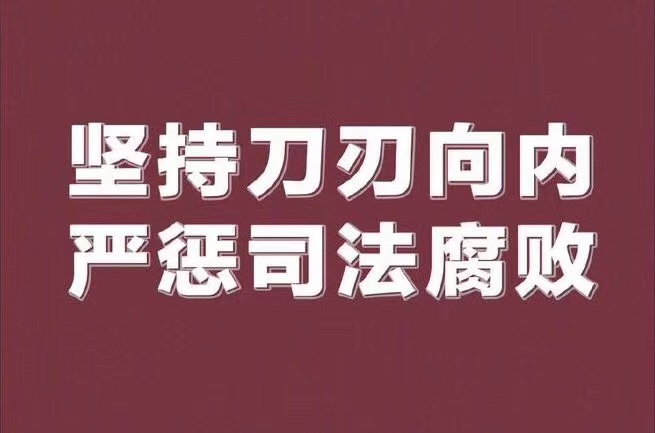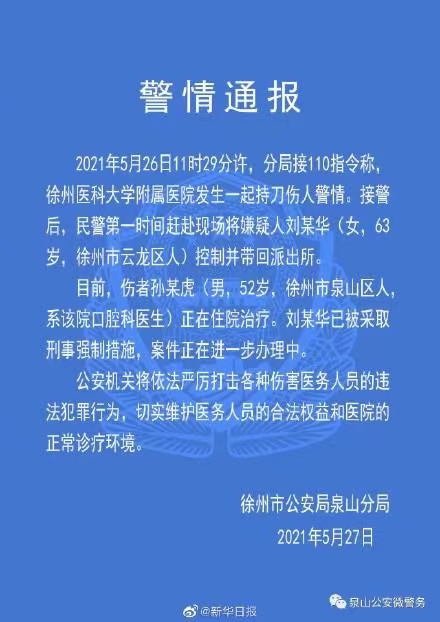“流动”儿童,卡在城乡之间

2月中旬,立春过后的北京仍然阴寒未尽。同心未来学习中心的老师们在这开学前的最后一周忙碌着,准备迎接新学期。提前返回北京的孩子有的已经回到了学校玩耍,尽管为了在开学前节约经费,暖气还未打开。同心未来学习中心是一所面向北京务工人群子女的活动空间,位于北京东五环外的皮村。这是北京市最知名的城中村,容纳了许多外来务工者,也出过育儿嫂范雨素这样的素人作家。
按照正常的节奏,春节过后,孩子们会陆续返回学校。这些儿童多是在北京工作的家政工、清洁工、保安、建筑工和个体商贩的孩子。近一两年来,受到疫情和教育政策变动的双重影响,北京市一批打工子弟学校受到波及,开开停停。

“读到一半,学校不让开了。”在2021年秋季学期,任文欣记得一些家长已经交完学费,完成报名。但突然学校收到通知,告诉他们不能开了。“我们又赶紧协助他们去对接其他学校。对接完了以后,学校又有风波,原来的学校表示还能正常开,所以有的学生又回去了。”任文欣是协作者困境儿童自助图书馆项目的负责人,这是一个为打工子弟提供阅读服务的公益项目。
劳动力转移,或许是过去40年间中国内地人口流动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来自乡村和城镇的劳动人口离开家乡来到城市,谋求更好的生活。与此同时,在庞大的迁移背景之下,流动人口的暗面是形态各异的家庭和尚且年幼的孩子。流动人口,又称“外来打工人口”“进城务工人员”,是还没有获得完全城市公民身份,徘徊在边缘的“异乡人”。他们被留在老家的孩子被称为“留守儿童”,而被带在身边的孩子被称为“流动儿童”。
2017年,21世纪教育研究院和新公民计划公益组织联合发布《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6)》,这是国内首部流动儿童蓝皮书。报告指出,截至2015年10月,全国流动人口总量达到2.47亿。而作为流动人口子女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两个群体总量约为1亿人。用更直观一点的数据来讲,每10名儿童中就有4名受到人口流动影响——他们就“流动”在我们的周围。
长期以来,中国的户籍制度扮演着控制人口流动、协调社会资源分配的角色。由于没有居住地户籍,流动人口的子女往往无法享有户籍儿童同等的受教育机会。选择回老家“留守”,意味着与父母分离;而选择留在城市,意味着要面对城市里艰难的升学路。
因为无法参加居住地的中考和高考,他们需要在初二或者初三时作出选择,在义务教育阶段结束后返乡、读职业学校或是进入社会。对许多流动儿童来说,辍学以及早早务工是他们可预见的命运路径。
2014年,国务院出台了一项户籍制度改革意见,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的落户限制,同时严控500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在人口疏解的背景下,许多流动人口被迫离开。
北京市就在当时提高了非京籍学生义务教育的门槛,并大规模拆除打工子弟学校。与珠三角地区更多源自工业化的劳动力流动需求不同,北京市的流动人口多集聚于第三产业,比如,餐饮、零售、建筑等领域。
在北京,以家庭为单位的外来人口一般都居住在城乡结合处,或者城中村这样的小角落。朝阳区洼里、太阳宫、海淀区八家都是典型,招收流动儿童的学校也多分布于此。
从2022年9月起,我们在北京市不间断地访问流动儿童学校、家庭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写下了这篇报道,试图展示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北京市流动儿童在城市中的“流动困境”。
01 漂浮感
一项针对小学流动儿童家长的调研结果显示,受访者在京的平均居住年限达到10.2年,然而,对这些外来家庭来说,长住10年并不意味着“稳定”,其心态和生计都处于动荡之中。对流动儿童来说,动荡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频繁转学”。
小姚是任文欣在工作中救助的一名流动儿童。因为爸爸要在外面跑外卖,她和姐姐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由于贫困,很多时候,小姚的晚餐都以“喝水”解决。
“我们经常自嘲,我们服务的群体是‘灯下黑’,你难以想象,在北京会有孩子连吃饭的营养都成问题。代际贫困一直在发生,尽管现在也有好的新动向。”任文欣说。
小姚之前就读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关停了,几经协调,她中途去了一个就近的公办学校就读。那是一所混合公立学校,部分承接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但这些孩子往往会被分配到一个班里,与城市里的孩子隔绝开。“老师会觉得你们的基础怎么这么差。”此前,小姚在打工子弟学校成绩可以排到中上等,但在公立学校,她成了“差生”。
“很多孩子会因此很受挫。我们就会帮他们制定学习计划,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班里的事情。差不多要大半年,他们的学习成绩才开始一点点往上追赶。”任文欣说。
在2018年,何冉所在的新公民计划公益组织开启了一项流动儿童返乡追踪计划,通过实地观察、访谈和问卷,追踪记录北京一所九年制民办打工子女学校新希望学校43位六年级毕业生在未来几年里发生的故事,了解他们在毕业后的去向和变化。何冉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从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开始,何冉和同事每周都去给学生上课,从辩论赛,到性教育课、电影课,何冉希望这些轻松有趣的内容能让孩子们有所收获,同时也能拉近他们彼此的关系。2018年暑假过完,这个43人的小学毕业班里有25人返乡了。而据2022年9月的统计,这群孩子中入读职校的有15人,继续升学的有23人,辍学的有4人,另外一名学生情况待定。
曹玉是何冉跟踪的学生之一。2022年4月从中职学校辍学后,他在饺子店、火锅店、烤鸭店都做过服务员,但没有一份工作干满半个月。6月的一个晚上,何冉收到曹玉发来的一张长椅夜宿照——鞋脱了,双脚翘在长椅背上,夜色朦胧。因为没地方落脚,曹玉只好睡在长椅上,他告诉何冉,自己又辞职了,这是他半年来辞掉的第五份工作。
曹玉是安徽人,在北京出生、长大,他的妈妈是天生的失语者。在何冉调查的43名学生中,选择继续升学的基本上都是成绩好的学生。但曹玉不属于其中,他本来计划在老家的职校攻读汽修,谋得一技之长。不过,读了没多久他就再次辍学了。
小升初开始,这些孩子就要面临分化的抉择,想升学的逐渐转回原籍,不想升学、计划打工或者读职校的学生就在学校里混日子。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学教授申继亮主编的《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心理研究》一书中提到,这种不稳定性往往会给他们带来一种漂浮感。

何冉记得,在毕业时,她和同事设计了一个告别环节,鼓励孩子们用照片记录在学校里的瞬间,提交照片的孩子会收到机构送的相册,作为一份有独属记忆的毕业礼物。何冉原本以为孩子们会很踊跃,结果根本没有几个同学感兴趣,“完全没有我们想象的那种很难再见到的离别氛围”。
“当我和这群孩子关系熟了以后,回推这段经历的时候会发现,对他们来说,分离是比较稀疏平常的事情。”何冉说,“有好多同学小学都换了好几所,也有一些是有留守经验,再从老家转学过来的。所以‘分离’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常态化的流动行为。”
02 入学的门槛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后称“协作者”)成立于2003年2月,是全国最早的民办社会工作机构之一。2003年,机构刚成立不久就遇上了“非典”。在那期间,协作者就开始做一系列“非典”救援,当时的目标是找到在“非典”疫情下处于困境的农民工。在寻访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大量的流动儿童。
在开展服务之初,创始人李涛跑遍了北京流动人口集中的地方,比如张万坟、黑桥村这样的城乡结合地区。“这些农民工的孩子往往都住在菜地里临时搭建的窝棚里。他们上的学校都是打工子弟学校,但那时学校的状况比现在差很多,放学回到社区也基本没人管他们,问题非常多。”李涛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说。
在城市里,流动儿童入读的往往是两类学校:一类是以打工子弟学校为代表的私立学校,一类是与本地学生共读的混合公立学校。从资质和教育质量来说,一般后者更受到家长们的青睐。但即使政府和相关部门放松了对流动儿童进入公办学校的限制,入学矛盾仍然难以解决。一方面,公办学校学位有限;另一方面,这些学校往往处于城市教育的边缘地带,大多在城乡接合部,大城市里的优质教育资源基本与流动儿童无缘。
目前各个地方的流动儿童入学政策大致可以分为“积分入学制”和“材料准入制”两大类。积分入学制即按照流动人口累积的分值,依据区域内的积分由高到低安排儿童进入公办学校入读。珠三角、长三角部分地区采用的是这种方式。材料准入制则是家长们在准备好符合政策规定的材料资质后,子女可获得本地入学资格。北京、天津、南京、武汉等城市采用的都是材料准入制的方式。
2014年起,北京市对于随迁子女的入学证明材料要求“五证齐全”,这五证包括实际居住证明、务工就业证明、户口簿、居住证、无人监护证明等等。根据各区不同要求,有时家长需要准备三十多份证明材料。其中,无人监护证明在2019年被取消,政策要求变成了“四证齐全”。对于务工人员来讲,其中相对难获取的是务工就业证明和实际居住证明。
“房东不给你(房产证)照片,最后托关系,又私下里多给了2000块钱,才愿意配合我们交这些材料。”白冰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每学期都有很多家庭因为各种原因孩子没有上到公立,都还在准备一些材料,所以会把私立学校当作过渡。”
两年多里,白冰已经为女儿换了3所学校,入学手续的办理总是因各种原因受到阻力。每当自己感到疲惫时,白冰都会想起参加活动认识的一位家长所述的情况——孩子留守在老家读书,经常旷课,到后期演化到上学就“自杀”的地步。白冰担心女儿也变成留守儿童,于是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让女儿在北京读完初中,留在自己身边。2022年9月,白冰终于在办齐手续后将女儿转入一所公立学校,可以稳定地读到小学毕业。
而对于更多对小孩的学业没那么上心的家长来讲,打工子弟学校成了流动儿童的落脚之地。与公立学校相比,打工子弟学校的学费较低,入学要求也相对简单。这些打工子弟学校由私人运营,学校经费主要来自于学生们缴纳的学费,但这些学校的教育质量往往让家长们担忧。
工资低、晋升机会和学校光环有限,因此打工子弟学校很难吸引到好的老师,“年轻的老师好不容易有点教学经验就离开了。学校的老师也换来换去。”据何冉了解,有的学校甚至还出现了“包班制”老师,即一个老师包下一个班所有的课。
北京市一所爱心希望学校的校长告诉我们,他的学校里几乎没有年轻老师,“年轻教师第一留不住,第二工资低,别人也不愿意来,他们的理想抱负不在这。我们这里的老师最少3年起步,10年甚至15年以上教龄的老师居多。”这些资深教师来自全国各地,往往都是随着家庭搬到北京,没有响亮的学历,大多是中师及以上。

不过,即便条件有限,打工子弟学校的存在至少能让孩子们在城市中有书读。
对于这些学校来讲,近两年更大的影响来自于教育政策的调整。2021年,出于实现教育公平,限制“掐尖”以及中高端民办学校和教培机构的发展,八部委联合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要求各地调减民办学校的在校生规模,并控制在5%的红线以内。这促使各大城市关闭以及清退了一大批民办资质的学校,打工子弟学校因其民办性质不可避免地成了受波及的对象。
“所有社会上细枝末节的政策实施,首当其冲受到波及的就是这群人。而且永远是挡在最外围,第一轮就受到攻击的这群人。”何冉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打工子弟学校关得更多。好多老师现在已经失业了,其中很多都来自被临时关掉的学校。”
据新公民计划统计,截至2014年,北京市一共有127所打工子弟学校,在校学生人数近10万,但自2017年起,《关于加强北京市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颁布,推动了民办校从主城六区向郊区迁移,大红门产业带的拆迁也造成大批学校腾退。其他学校陆续因为没有办学资质、不符指标或因学校拆迁渐渐退出。以流动人口比较聚集的大兴区为例,2004年时,这里还有4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如今留给流动儿童的,“只剩下一所中学、两所小学。”前述爱心慈善学校的校长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截至今年2月,记者陆续拨打了北京十几所打工子弟学校的电话,都因关闭而无法取得联系。
受到打击的不仅仅是学校,建在打工子弟学校内部的图书馆也受到了冲击。因学校运营复杂,为流动儿童开设图书馆,试图为孩子们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阅读环境成为部分公益组织妥协的方式。微澜图书馆是新公民计划旗下开设在打工子弟学校及城乡结合部社区中的公益图书馆,原本在北京有43个分馆,目前只留下十来个,大多集中在北京的远郊。“有的新馆在暑假已经建好了,结果第二天学校说接到通知说不让办了。”微澜图书馆的对外合作负责人吴丽丽说。
03 支持者的挑战
在做返乡追踪项目时,何冉发现,更大的挑战其实来源于孩子们的家长。每次回访,何冉都需要不停地向家长们解释,也会碰上非常不耐烦的家长,“他们会觉得你做这个事有什么用?有的家长会说,你不用打电话来了,孩子没什么事,都挺好的。”
在市场和政府之间,往往是社区机构这样的公共服务部门在补充缺失。以新公民计划为代表的社区机构所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此前,新公民计划曾经开展过两个学校项目,一个是支持教师教学,另一块是提供托管服务。选择做“托管”是因为只有把握住孩子们放学和节假日的时间,社工和志愿者们才有机会直接接触家长和孩子,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和思维施以影响。但作为一家社区机构,从校方这里获得信任需要很长时间,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项目的推进。针对毕业后流动儿童的追踪项目就是在教师教学项目结束后的尝试。
另外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机构在运营过程中的资金困难。“不管是我们的课程还是图书馆,主要面向城中村的低收入群体,大多不收费或只收取普惠价格,目前还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所以在2020年以前,我们没有稳定持续的经济来源,只有一些朋友、爱心人士和企业捐赠少量资金。”同心儿童友好空间创始人王博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说。
王博是一名85后,来自河南北部的一个贫困小村。2012年,他参与了一个公益项目,走访城中村里的打工子弟学校。那是一个狭小局促的教室,课桌用长木板和砖头垒起来,孩子只要一动,就会吱呀作响,和他小时候读书的环境一样。那个炎热的下午让王博记忆犹新,他没有想到,经过了20年,竟然还有孩子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读书。也是从那时起,关注“打工群体”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2015年,王博筹备开设了图书馆这个小空间,位于同心未来学习中心的后院,是一个为流动儿童提供阅读、交流,以及培养生活技能的地方。图书馆初建时主要靠王博和志愿们利用业余时间来运营,人力和运营成本较低。但在2020年疫情之后,一些原因使得同心图书馆需要独立承担包括房租、水电,以及全职的人力成本。没有了减免房租等优惠措施,自负盈亏的压力架在了王博肩上。

“2020年对我来说是个至暗的时刻,内部外部都有非常多东西对这件事产生冲击。”为了把同心图书馆办下去,王博一方面要从外部寻找资金,一方面从内部重新设计,并开发一些能增加收入的课程和项目,会员制就是从2021年开始尝试的,每月50元,此外,他们还做夏令营、自然体验,以及一些城市游学类的收费课程,才勉强在这两年里让图书馆正常运作了起来。“资金很重要,我们每个月都在筹集图书馆的房租,资金会决定你维持这个事情的时间,以及能不能给需要的人提供及时的服务。”王博说。


无论图书馆还是托管中心,都需要社工来维持稳定的运行,而社工人才的培养需要时间和实践经验的积累。任文欣发现,社工群体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在于,往往在入门后三五年,社工们能独立开展工作了,但这也是他们需要结婚成家的时间点。“我们有非常多经验丰富的一线社工,生了孩子后只能选择回到老家。成家后要在北京生存,压力是巨大的,这也导致了社工人才的流失。其实我们大部分也算是流动人口。”任文欣说。
04 返乡之路
因为户口和居住地分离,对于流动儿童来讲,他们在城市中的升学路径艰难。从幼儿园入园开始,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每一道关卡都是一次挑战。如果父母闯关不成功,或是意志不够坚定,一家人随时有可能面临分离,流动儿童成了留守儿童。
近两年,受大城市户籍和教育政策的影响,很多长居城市的流动儿童纷纷回老家就读,以便提前适应本地教育和升学考试,这类儿童被称为“回流儿童”。2015年以来,流动儿童的教育政策由“两统一”转为2019年的“推进随迁子女待遇的同城化”。从表面上来看,流动儿童的处境正在好转。但众多学者近年来的研究又表明,对于这些儿童来说,“离开”城市依然是主流选择。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市场经济更活跃的上海。共青团上海市委的一项统计显示,上海的农民工子女初中毕业后面临3种选择,只有少数成绩较好的学生回到老家考高中,有5成学生在上海与父母一起经商、帮工或进入职业学校,其余则直接被抛入社会。
“错位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国家有‘两为主’政策,要求城市政府要不断提高流动儿童就读于公办学校的比例,那就有两个策略——一个是做大分子,让进入公办学校的儿童越来越多;另一个策略是缩小分母,比例就提高了。”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物学院教授熊易寒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说。“做大分子,让更多的流动儿童就读于公办学校,实际上是在提高市政府的成本,需要投入财政支出,那么要达到要求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减少分母,让更多孩子离开城市以后,就读公办学校的比例自然就提高了。所以做小分母也就成为很多地方政府在大形势下的一种选择。”
熊易寒读博期间在上海市的一所民办学校担任过志愿者。这所学校曾受政策影响关停,六年级生全部转移至一所公立学校。成绩好的学生被分散插入其他班级,其他同学则被统一编入新班。这些学生也被公立学校的老师吐槽“基础差”,跟不上的同学则会被“退回”到流动儿童的班级。熊易寒发现,很多流动儿童都认为自己不应该和城市儿童一起玩,他们会主动维护二者间的社会边界。
熊易寒认为,这是出于孩子们的自我保护,“为了逃避在跨群体互动中被强调外地人的身份,他们宁愿主动跟本地小孩隔离,不跟他们玩,从而维护身份上的差异。”
熊易寒在调查中发现,无论在学校还是社区,农民工子女都很少有机会与城市同龄人交往。原因在于,虽然农民工子女就读于公办学校的比例越来越高,大部分学校对农民工子女单独编班,有的学校甚至会把作息时间和本地学生班错开,以至于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同龄人很少能接触到。
对于城市里的流动儿童来说,一方面,父母忙于生计,疏忽了对孩子的陪伴与照护,流动儿童得不到有效的督促和引导;另一方面,他们在学习上两极分化严重,只有少部分孩子学习习惯良好,大部分人的自主性和上进心均不强。
有学者认为,导致流动儿童厌学,或者觉得学习没有希望的原因在于:首先自身教育基础不好,而这往往由经常流动或转学造成;另外,家长的教育理念落后,不重视子女的学习;且由于户口限制,家长和孩子都对求学不抱有期望,因此“破罐破摔”。
已经辗转入读公立学校的小姚最后还是迫于现实,返回了老家。除去教育政策的变动,在此前的疫情管控下,父母的生计是更大的难题。尽管家里人都希望能把孩子留在北京读书,方便照顾,但小姚爸爸所在的公司不给他缴纳社保,小姚也就失去了继续在公立学校就读的资格。全家人在商量过后还是把小姚送回了老家。
有学者分析,许多流动儿童一出生就跟随父母在城市生活,一旦回到老家,“可能被巨大的陌生感和无助感包围”。对于一年回一次老家的他们来说,家乡并不是亲切温暖的。
何冉也在今年发现了有意思的点,新希望学校被拆后,大部分学生转学回到原籍,而初二回去的这一批学生“没有一个是适应环境、交到朋友的”——他们与同学的关系并没有延续到生活中——没有一起骑自行车回家,也没有在周末一起去公园。“相比留守儿童,这些回流的孩子更孤僻,在同伴关系上表现得更差。”
除去老家经济发展水平低、就业机会少,流动儿童也会在访谈中提起老家交通不方便、下雨天出门泥多把鞋弄脏等话题。“这其实表明流动儿童早已经认同城市的生活方式,老家农村的生活方式已经离他们越来越远。城市在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塑造着流动儿童的心性、气质、观念和认同。这些流动儿童无法像父母一辈那样把老家当作自己的归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卢晖临团队在2015年发表的一篇研究中提到。
选择留守,他们要面临的是陌生的老家和远离父母的生活;而选择流动,他们面临的是难以安稳的教育现实。对于很多流动儿童而言,退守老家的选项已经消失,因为城市不是他们的短暂栖息地,而是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在返乡完成学业之后,部分流动儿童又重新回到城市,重复父母务工的老路。值得注意的是,因还涉及到与城市本地人口的资源博弈问题,在公众议题讨论上,流动儿童相比留守儿童更为边缘,且难以像留守儿童问题那样更容易达成共识。
(实习记者陈虹羽对本文亦有贡献)
作者: 崔硕、文思敏
来源:第一财经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好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致信jinrizhiyi@gmail.com,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