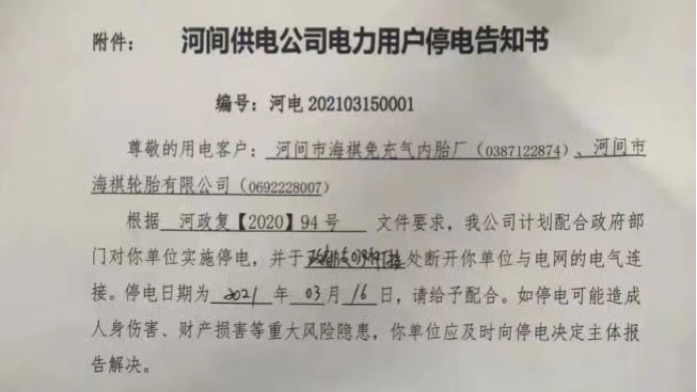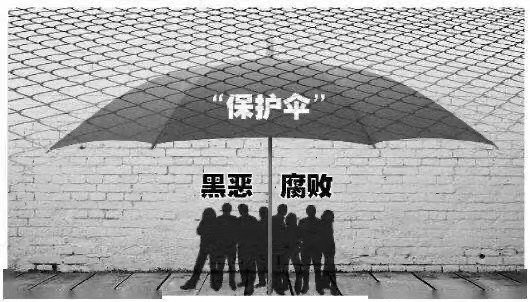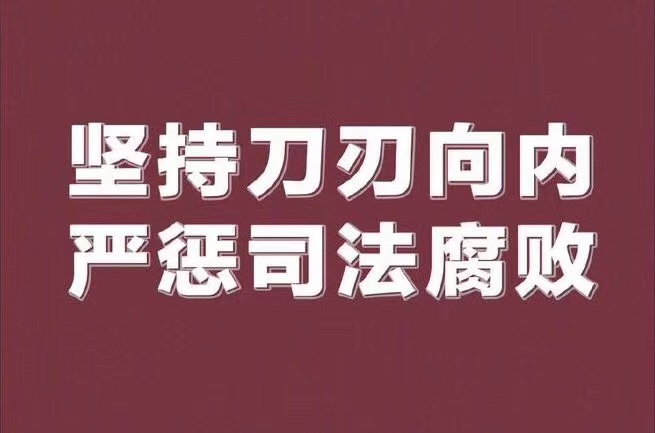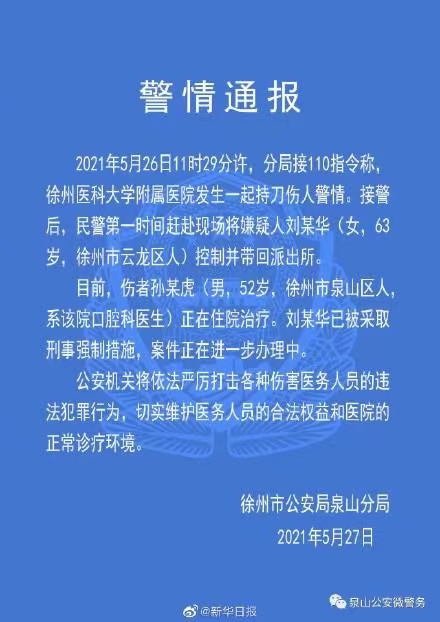他们终于对摇滚下手了



石家庄当局对摇滚的政策性利用,以一己之力,将大陆摇滚的社会面向扩展到“荒诞”的程度,可以说无形中令摇滚的精神旨趣一骑绝尘,又让摇滚在音乐层面上追无可追。这是现实卡死摇滚站位的绝好案例,杀死那个石家庄人,自此有了双重喻义。
在理解石家庄建造“摇滚之城”的动机时,在明面上它确实源于无名之城对流量时代的应激反应。淄博凭借烧烤这个不健康食品,以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出位一跃,在汤汤流量潮中轻取一瓢饮,足以让下位城市眼红、上位城市心痒,石家庄反求诸己。
但一个可能无法摆在台面上的问题是,摇滚本是独立、反叛、抗拒主流的文艺方式,敢问它何德何能,会被官方择定为立身之本?从石家庄召开的省市摇滚乐座谈会看,似乎有摇滚圈内人士鼎力相帮,令人遥想摇滚行当里也出及时雨。
大众都在取笑,摇滚这个反体制的东西,竟然被体制内当作香饽饽,表面看“摇滚之城”的文件精神中满是悖论,非扭曲逻辑不足以畅想摇滚巴士穿行石家庄的情景设计。可若从流量的角度去想,而不是从摇滚伦理出发,一切都讲得通了。
“摇滚之城”的创意,其底色依旧是流量为王的城市文宣模式。这种文宣模式混合了诸多时代的病症,如取媚年轻人、追赶短视频传播的中老年心态、在线投身内容泡沫的时髦等。剥去其外在的越来越短的流行周期,城市文宣的焦躁感爆棚。
在摇滚之城这个大饼被画下来之前,流行的是淄博烧烤,在此之前,则是各地文旅局长的变装秀。在流量时代的狭路相逢中,原本只有媒体承受着流量高压,现如今,行政方阵加入到流量施加的虐恋中,并且以更加激进、也更加悲哀的姿态应和群氓。
将完全不属于自己的摇滚划入流量政务的蓝图,人们议论最多的是两下气质的冲突,但要看到,就行政力对流量的控场、以及因此衍生出的网络自信而言,这种蓝图描摹又是“贴切”的,毫不违和的。摇滚搭台,流量唱戏,摇滚只是工具而已,跟烧烤架无异。
摇滚之城中的“摇滚”,并非爱好者念兹在兹的那股野生的、个性的力量,而是行政者予取予夺的流量工具。一切流量都可以为我所用,这是“摇滚之城”主导者的成竹在胸。以流量来理解“摇滚之城”看似荒谬的设想,所谓冒犯都是自以为是,是认知失调。
反过来说,“摇滚之城”能在多大程度上伤害“摇滚”,恐怕是个伪命题。一来,“摇滚之城”倚重的多是伪摇滚的皮毛,是要与大众打成一片的摇滚类矫饰,与真摇滚无关。二来真摇滚的有无、多少,连摇滚人士都争论不休,遑论伤之?
但“摇滚之城”的石家庄创意,确实激起了摇滚为何物的浅浅涟漪。遗憾的是,摇滚的流行化、大众化乃至流量化,从未在思想层面结出可靠的果实,总是在流量喧哗中习惯性流产。官方建造的“摇滚之城”,与个人心中保守的摇滚堡垒,隔着流量的星河。
即使“摇滚之城”与真摇滚无涉,石家庄在冲击流量池的同时,也不能说没有尴尬。这份尴尬的唯一挑战、或者说突出障碍,是一个具体问题,就是如何圆润地处理万青乐队的“杀死”之句。是保持“杀死”原样,还是用“口死”取代之,成了“摇滚之城”的气门芯。
看到石家庄的官方制造,已经用“杀不死”之谓来冲淡“杀死”的民间气质,其用心良苦,其效果相当摇滚。所以说,石家庄在华北平原搞的“摇滚之城”的实验,散发出早期革命主义的浪漫情怀,又以时髦的流量追求贡献出特有的华北景观。
“摇滚之城”设想的提出及其初步展露的社会景观,令这一行政纲要具备了迷人的赛博外貌。若要透视“摇滚之城”蓝图的本质,你会发现在它的核心深处一无所有,但这种由内而外折射的虚无与俨然,又具体而微地见证流量时代的堂皇,这是它比淄博烧烤高级的地方。
目前,石家庄对摇滚这个异类、少数派、不服来辩所交出的纸上实验作品,雄辩地证明一种风尚,在“技术无好坏,关键看谁在用”之后,流量也沦落到此种道德虚置、伦理豁免的境遇中。内地摇滚不振已久,而由石家庄官员掀开摇滚史的新篇章,就问你嫉妒不嫉妒?
作者|宋志标
编辑|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