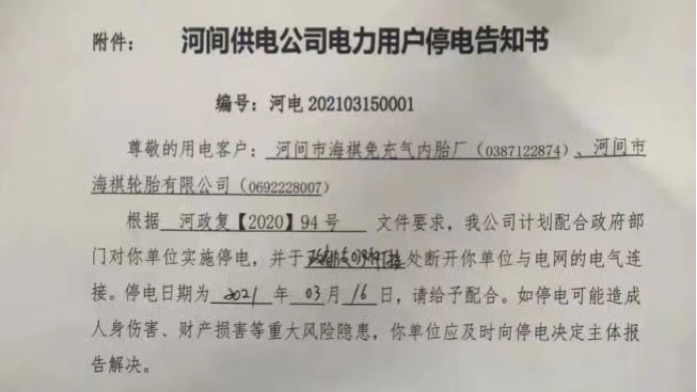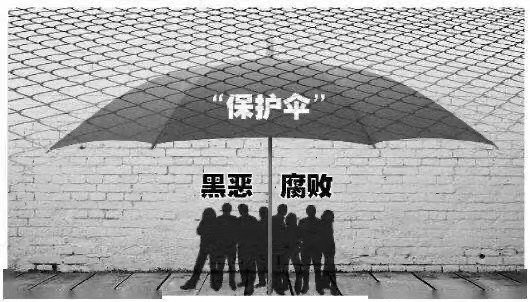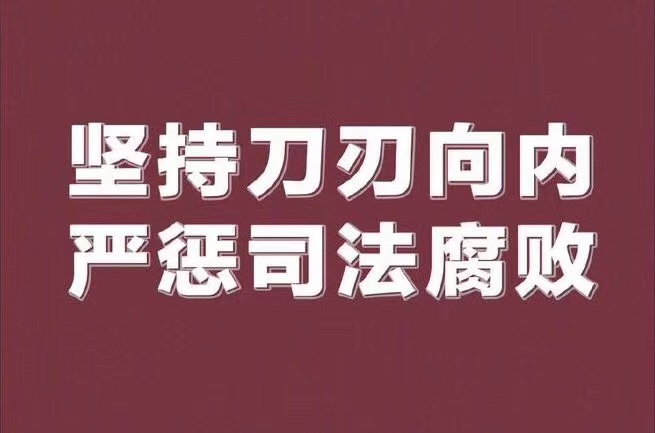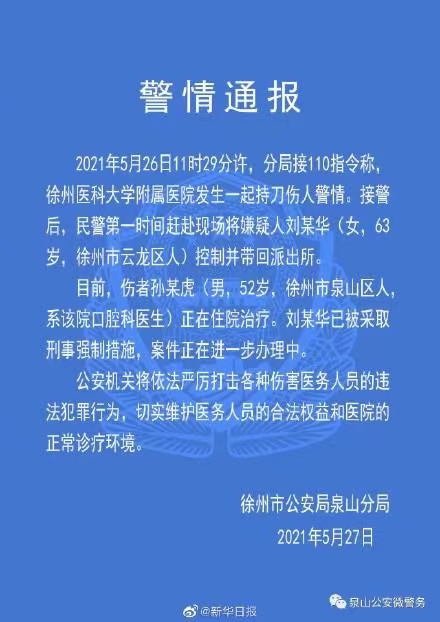张从文:郑州无祭


乘一号线地铁渐近郑州火车站的时候,我无端地有一小会儿冷颤,感觉车箱里的冷气很足;乘五号线地铁渐近沙口路时,我又有一小会儿冷颤,心里便明白过来,这与冷气无关,与今天七月二十号这个日子有关。
①
郑州火车站西广场的地铁C出口,距京广北路隧道的南出口只有500米,上午正炎热,车辆匆匆,行人寥寥,偌大的街市似乎只有我一人心有所系,蹒跚绕走,用手机对准隧道出口照来照去。俯身下看,一道狭长幽深的大斜坡沟槽,像一具沉重的棺材;凝神隧道深处,灯影恍惚,一些小车零星驶出来,像要漂起来的样子,在我眼前交叠出两年前洪水漫灌的景象。那时,这道城市的伤口溃烂得无法收拾。
跟我同行的林子,热得难受,顾自在树荫下呆立,巴不得我快快离开。
林子从小跟我学琴,极其听话。现在读大学了,暑期还来找我。我问:7.20时你在哪儿?他说:在家上网课。之后坐爸爸的车来过这里,但不是为了看灾情,只是路过。我又问:你爸爸当时在哪儿?他说:在家。因为有疫情,报社没有安排下去采访。我知道,在省内第一号大报里工作不容易,没有为京广路隧道写点什么不是他的错。
我在这个北进南出的双向车道边绕行一圈,没有行礼默哀,只是用手机四下拍一些带字的标牌。唐山大地震、汶川大地震都立了纪念碑,98年抗洪还在长江沿岸多处立碑建塔,为什么这一场震惊中外的特大雨灾不予纪念?哪怕只在交通标志底下写一行字,也好叫那些无辜失去生命的人,不至于像春雪化水一样被世界遗忘干净。回来想一想,大约天灾无法责天,人祸有法咎人。40年前的板桥水库也是这样不留一字,免了多少无可凭据的说三道四。
京广路从中原路到南三环,长6.5公里,有三处隧道,雨灾时一律灌满黄汤。其中以火车站这里的隧道人多车多,情形最为惨烈。排水处理现场时,警戒隔离范围很大,只有附近居民从高楼窗口拍得一些模糊的视频,看见拖出的车辆,有小车有公交,难以计数;至于哪些车上有罹难者便不得而知。
当灾后有关部门公布全省死亡人数,并且因高层下派检查团,几次紧急更改数字后,百姓有理由怀疑和不相信。但我的朋友老廖坚持说,公布的人数绝对可靠。他在市公安局做刑事警察,曾亲眼看过沙口路地铁里的事故现场。京广路隧道他没去,但那都有姓名有血样有照片,决不会出错。我这朋友是实诚人,就因为实诚,快退休了还是个普通警员。按咱们的游戏规则,一个层级只了解他可以了解的事情,可以肯定,他所认定的跟允许普通公众知道的范围差不多。
②
我给同学的儿子岳扉发微信:“今天7.20祭日,正在去京广路隧道和沙口路地铁站的路上,你愿同行吗?网上见有民众献了一排鲜花。”等了许久没有回复。
从地铁一号线转五号线,感觉车站的治安巡警多一些,车箱里,他们穿着淡绿色荧光背心来回走动,警靴着地有力。
沙口路有5个出站口,我和林子随机选C口出关。在电梯底下的一角,我见两个穿红色马甲的工人蹲靠着,就过去请问:从这儿上去,哪里有献花的地方?俩人扬起头来,其中一人面容方硬黎黑,不客气地说:“没有,没有!”我打量他的样子很像鲁智深,心想是不是打扫卫生挺让他屈才?我们上电梯时,他俩也随后上来了,跟另外4个红马甲一道,在几排共享单车旁无所事事地闲走扇风。
越过自行车,一位穿深色衬衣的中年男士坐在小马扎上,样子比这些红马甲斯文。我过去请问:沙口路站献花的地方在哪儿?那男子一懔:“你是来献花的?”见我只是挎了个包,就问:“你的花呢?”我说我只是来看看,因为在网上见许多人昨天来献花了。男子的神色松驰下来:“昨天是有人来过,都被劝退了,这里没有献花的地方。”至此,我的榆木脑袋终于开了条小缝儿,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便衣警察。我微笑:你在这里有公务?他不置于可否:“没啥事,在这里歇会儿。”
我心有不甘,离开他返身在沙口路站牌柱下用手机拍照。这时,另一位穿白衬衣的青年男子走过来:“别照,别照,请配合一下。”他倒不装了,也没有发脾气:“快离开,快离开!”
我执着于拍照路牌和站牌,跟在京广路隧道口一样,开始相信路名和站名就是纪念碑,就是无言的说明文字。两年了,那些凄惨的影像、图片和文字,与这里的路名站名已然融为一体。
京广路隧道排水后,车辆杂陈,有人辨认出亲人的遗骸,哭喊得撕心裂肺,比刀子扎人更疼!
蓝色雨衣人夜坐沙口路站口,在自行车上插纸板:“妞妞,爸爸还想接你回家!”
这些事不敢回想,一回头就有眼泪要流。
当我被便衣阻拦和驱赶的时候,想起了出门时内人的嘱咐:今天肯定会有警察,离远点,别惹事,林子今后还要进行政事业单位的。
③
收到岳扉回复的微信:“我记得上次这种事情后来被驱逐了。”
他的判断不错,现在再有这种事,也会被驱逐的。但他忘了,去年曾有民众合力拆除了架起的隔离挡板。岳扉年纪轻轻在家赋闲,学习炒股。从他的简短文字可以看出一种置身事外的态度,我于是回复:“见到一些治安人员,便衣倒还客气。”之后再没回应。
沙口路地铁站的C、B两出口,分置于黄河路两边南北相对。离开C口时,我四面看看,的确不见哪里有鲜花,甚至没有人驻足于此。径直过到对面B口,想起之前在网上见有一张7.20周年时民众献花祭奠的图片,花就摆在B口台阶前。现在这里空荡荡的,无端站着5个身穿黑衣却像民工的中年男子,有的擦汗有的喝饮料,闲散无事。
进站口旁边树荫下,有年龄较长的小老头和老大妈,一人穿一件红马甲。我见老头儿和善,便走过去问他:这红马甲是啥时候开始时兴的呀?我的意思是协助交警守路口的大爷大妈都穿淡黄色马甲。老头呵呵一笑:“才发的。这大热天非叫社区组织人来这儿守着。”我装做惊讶:门口都是你们的人?老头含含糊糊:“有他们的人,也有我们的人。”所谓他们,当然就是便衣。我顺势问一句:这里是不是有人献花?老头儿还是陪笑:“不让不让,等过几年政府准了你再来吧。”我并没有说我要献花,他却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职责。好吧,我也向他笑笑,和林子一道走下地铁台阶。
地道里空荡荡难得见人,灯光四壁反射似乎摇摇晃晃,空寂惨淡,正好让我设想两年前的今天,从地道深处传来的失魂落魄的哀嚎和泥滑水湿的跌爬与奔跑。叫声最凄厉的,应该是“妈呀——妈呀——”,这让我想起自己的母亲来,眼泪便禁不住在眼眶里打转。
远远地走来两个红马甲,抵近时认得,正是在C口里见过的鲁智深等两位。他们也认出我来,那眼神有点狠,像在说:转什么转,滚远点!唉,我们素昧平生犯得着吗?这实在有点近乎于疫情封控期间人们深恨的“底层互害”。
我这样议论或许太苛刻,因为他们不过是为了一份短期的额外口食。记得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特性》中说,中国人缺乏利他主义,原因在于普遍的贫穷。“维持生存的压力,以及由于这种压力而养成和定型的生活习惯,甚至在直接的生活需求不再紧缺后,也会使生活水准降低到艰难的仅能维生的最低限度。……钱和粮是中国人社会生活楕圆上的两个焦点,并且是所有人社会生活中的重心。”
时代几经更替,我们在钱粮面前,仍然坚守着自己不利他的特性。即使是那些在灾难中不幸逝去的生命,也曾经和我们是一样的人啊。
慎终追远,我们对自己的不良特性深怀嫉愤,却又不得不深爱这样一群人,因为不爱,我们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向真正的文明。
【作者简介】张从文,二胡教师,一枚园地耕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