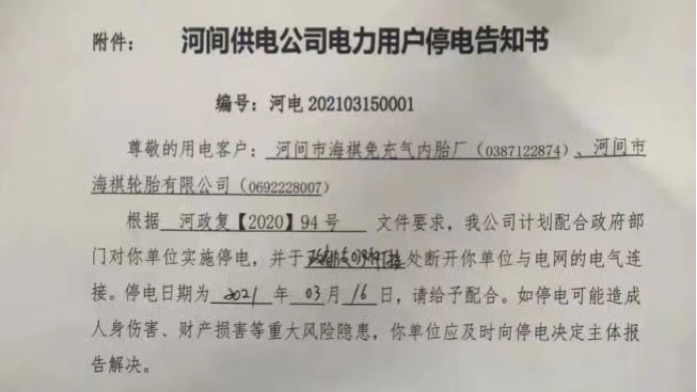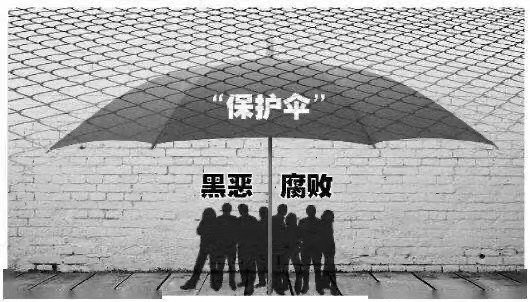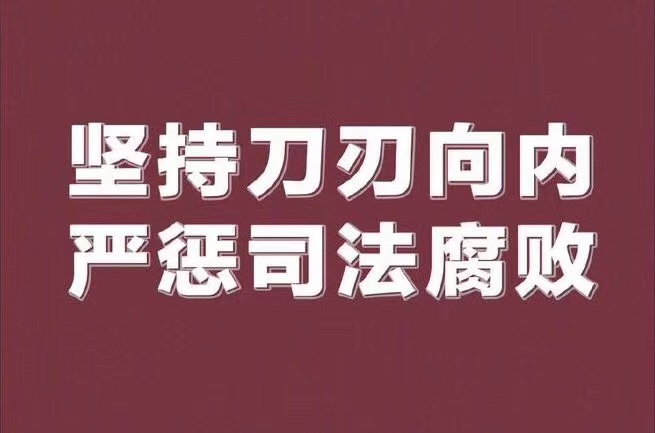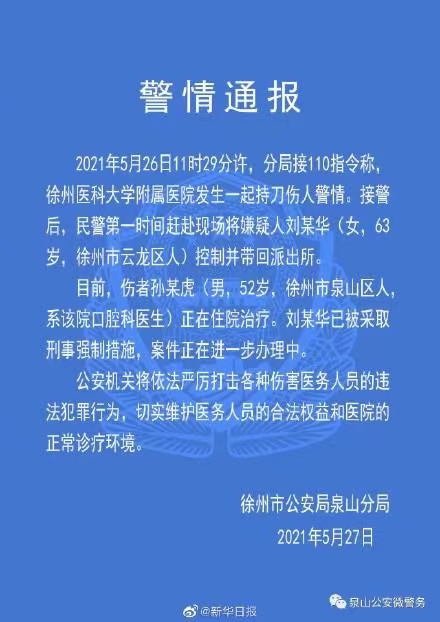从“疑罪从无”到警察特权:评济南司法局李爱新对邢志强案的错误解读


在最近一篇题为《与邹丽惠律师商榷:警察盘查迥异公民扭送,疑罪从无岂容“故意杀人”?》的文章中,济南司法局干部李爱新(网名“安在”)对内蒙古警察邢志强1995年枪击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试图通过混淆警察职责与公民权利的界限、美化警察职业的特殊性,以及曲解“疑罪从无”原则,为邢志强的行为进行辩护。然而,通读全文后,不难发现其观点充满了逻辑混乱和法律误区,对司法公正的维护造成了严重偏离。
一、警察履职行为与公民扭送:李爱新的混淆逻辑
李爱新在文章中反复强调,邢志强当年的盘查行为属于《警察法》规定的履行职责,而非公民扭送的行为。她通过引用《警察法》第九条和相关规范,试图证明邢志强的行为是依法履职。然而,她却刻意忽略了一个核心问题:警察履职行为必须符合合法性与规范性,而非仅仅基于“穿着警服”这一表面特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九条,警察履行职责时,需在规定范围内执行法定任务,且必须遵守执法规范。而邢志强在案发时并非处于值班状态,且携带步枪打靶,这一行为显然与履行公务无关。他在非工作安排的情况下,擅自对嫌疑人进行盘查,并导致事件升级,无法简单归类为合法履职。

更值得关注的是,李爱新将“公民扭送”贬低为一种不需合法性的见义勇为行为,模糊了公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界限。事实上,公民扭送是法律赋予普通公民的一项权利,而警察履职行为则受严格规范约束,二者在法律依据和适用场景上有本质区别。李爱新的观点不仅混淆了这一区别,还为警察权力的任意扩张提供了理论支持,这种解读是极其危险的。
二、“疑罪从无”原则:岂能任由主观臆测?
“疑罪从无”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石。然而,李爱新在文章中对这一原则的解读充满矛盾和误导。她一方面承认证据不足时应适用疑罪从无,但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主观猜测和推论为邢志强开脱,甚至声称“无法证明是正当防卫,但也不能认定为故意杀人”。
她的逻辑错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对证据标准的误解:李爱新声称“枪击造成孟永清非致命伤,其延误治疗致死与邢志强放任行为无直接关联”。然而,她未能提供确凿证据来证明这一论断,仅凭“可能性”便试图替代法律所需的明确证据。这种推测不仅违反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也进一步弱化了疑罪从无在案件中的核心作用。
2、用主观推测取代证据链:李爱新在文中提到,“无法排除邢志强在50米外开枪追击孟永清,导致背后中枪的可能性”,但这一猜测并未得到弹道痕迹或其他技术证据的支持。她的论述更多依赖对案情的主观演绎,而非基于案件事实和证据的严谨分析。
3、混淆司法责任与职业特权:她试图用邢志强的职业身份(警察)掩盖其在案发时可能存在的责任缺失。这种逻辑不仅对“疑罪从无”原则的适用造成扭曲,更容易引发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质疑。
三、警察权力与司法公正:谁在为特权开脱?
文章中,李爱新用大量篇幅对警察职业进行情感化辩护,试图通过美化警察群体的牺牲与奉献,来淡化案件中的司法争议。例如,她提到“穿着警服的警察是社会安全的象征,不能苛责警察在现场的临时判断”,试图将邢志强的行为合理化。
然而,警察职业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扩大权力边界,更不能成为司法豁免的理由。一个健康的法治社会必须严格规范警察执法行为,确保执法权力不被滥用。李爱新的观点忽视了这一基本原则,反而试图将职业身份作为免责依据,这不仅与现代法治精神背道而驰,也损害了公众对警察群体的信任。
四、司法独立性:避免情感干扰与舆论误导
李爱新文章中体现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她对司法独立性的忽视。她在文中多次提到公众对邢志强案件的情感共鸣,如“邢志强只想做一名好警察”,试图通过煽情语言引导读者对案件的倾向性判断。然而,司法裁决应以证据为核心,舆论情绪不应成为司法公正的干扰因素。
此外,她的建议——通过赔偿孟永清家属来平息舆论,也暴露了其对司法责任的模糊认识。赔偿固然是解决社会矛盾的一种方式,但它无法取代司法判决的法律效力。过分强调赔偿反而可能导致司法程序失去其应有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五、守住法治的底线,回归司法理性
司法的核心在于公平与正义,而非为职业身份或情感共鸣开脱责任。李爱新在文章中对“疑罪从无”原则的错误解读,以及对警察职责的混淆辩护,不仅暴露出其法律逻辑的偏差,也为司法体系的公信力敲响了警钟。
现代法治社会必须以证据为核心,坚守法律原则,而不是依赖职业身份或个人观点来替代司法独立性。对邢志强案的讨论,应该着眼于事实与证据,而非情绪化的辩护或对职业群体的盲目偏袒。
期待相关司法机关能够以此案为契机,强化执法规范与司法独立,真正做到以法治促公平,以公正树信任。这不仅是对邢志强案件的回应,也是对每一位公民法治期待的郑重承诺。
作者|林国行
编辑|程军
声明|本网站发布此文旨在传递更多信息,若您发现内容有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立即致信jinrizhiyi@gmail.com,我们将迅速核实并进行更正或删除。感谢您的监督与支持!